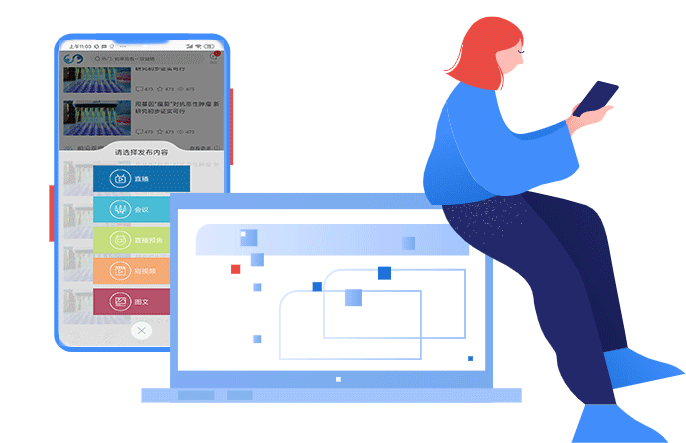不问来路,只问归处。

【已授权,使用请咨询画师】
壹
收养阿若后,我祸国妖姬的名头后又跟了个蛇蝎妇人的称号。
他们说我是在捧杀阿若,把一个冷宫里出来的小公主捧的无法无天,毫无自知之明。
其实不是的,我是真的想宠着阿若,想把这世间最好的东西给她。
再说,我一个战败送来的和亲公主,又哪里配得上祸国妖姬这样的“赫赫声名”。
我记得刚来北稽的第一个月,老皇帝很宠我,连着一个月宿在我的宴和宫。
故而在某个请安的日子里,侍女奉上了滚烫的茶水,我一个没接住,茶盏碎在地上,叮叮当当,随之而来的便是安贵妃的呵斥声。
老皇帝的后宫莺莺燕燕也不少,可元后仙逝后,便是安贵妃独掌大权。
我知道她是在警示我。
所以我毫不犹豫的退下,跪到了门外。
那天是个大雪天,我站在廊下,看着雪地里早已跪着一人,大雪落了他满身,却更衬得他眉目如画,比我三哥那满宫的美人都要秀气上三分。
安贵妃这惩罚人的手段当真是贫乏了点,动不动就是罚跪,也没点新花样。
我挑了个合适的位置,跪在那个少年旁,想着有他还能挡一挡风。
可是大概是我天生运气不佳,我刚刚跪下,便有公公远远走来,恭声道:“殿下,时辰到了,咱们可以回了。”
我看着公公扶着那个一瘸一拐的少年远去,原来他便是元后留下的倒霉孩子,太子成轲。
我这厢还在感叹成轲遇上一个拥有成年皇子的安贵妃,只怕没有什么好下场,忽然一股冷风刺来,从手指冰到头发丝,无一不在提醒我,先可怜可怜自己。
我抬头望着这漫天大雪,掐了掐早已冻得没有知觉的虎口。
干脆心一狠,眼一闭,就这样倒在了皑皑雪地中。
谁知道安贵妃的心更狠,眼一闭,全当没看见。
那次我在雪地里躺了几个时辰我不记得了,只是自那以后,我的左耳得了严重的冻疮,一到冬天暖屋里,就挠心挠肺的难受。
后来我伏在老皇帝的怀里撒娇哭泣,老皇帝搂着我唤心肝,赏了我如流水的礼物,而后转头却只是轻轻呵斥了几句安贵妃。
自那之后我便知道,老皇帝是个靠不住的。
相比我那拥有着三个成年儿子,夭折过无数皇子,常常叹子嗣缘薄,以此广纳后宫的父皇,老皇帝算是真的子嗣不丰。
除了安贵妃所生的二殿下,便只剩那个娘没了,爹不爱的太子殿下了。
所以我也别无选择,我只能选他。
我明里暗里不知帮了成轲多少忙,可惜这孩子是个不记好的,遇见我紧守宫规,低眉行礼,末了还要指责我一句:“宴娘娘不必如此。”
那一年里,我愣是没和成轲说上几句话。
不过他倒也不是没良心的,投桃报李,在我被安贵妃罚跪时,他也会使人悄悄通报老皇帝。
我们虽无太多交流,却是培养出了互帮互助,共抗安贵妃的默契。
我入宫的第二年,安贵妃办了好大一场中秋宫宴,很是亲力亲为。
然而一般安贵妃使了力气的宴席,基本上都宴无好宴。
这时我和成轲都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应对,可是一个没留神,成轲还是不见了。
宴会上觥筹交错,老皇帝喝的半醉半醒,我实在放心不下,偷偷离开了宫宴。
找到成轲时,他正拿着一壶茶水狠狠的往自己脸上泼,水珠从他的发梢滑落,顺着泛红的脸颊滑到下颌,然后滴答一声落在前襟,濡湿了大半衣裳。
我忍不住侧过头,却又看了眼躺在床上了,衣衫半退的铮铮铁汉。
我又忍不住转头,真真是没眼看。
没想到安贵妃如今的手段已经升级成这般段位了。
此刻屋前没人看守,想必是为了之后方便捉奸,我连忙扶住已经有些神志不清的“奸夫”成轲逃离灾难现场。
成轲的头点在我的脖颈处,沉重的呼吸声在我耳边无限放大,他双颊滚烫,碰到我冰凉凉的脖子忍不住蹭了又蹭。
我一把拍过他的脑袋,连忙带他拐进一个废弃的宫殿。
刚一进去,他又凑上前来,我推他不动,干脆甩了他两个耳光。
这两耳光我没省力气,成轲似乎清醒了一点,看了我一眼,低声唤道:“宴娘娘。”
“清醒了…”我还未说完的话,尽数被堵了回去,成轲的气息突如其来得侵袭了我。
我一直把成轲当成倒霉孩子,但当他锢住我的手,展现出绝对的力量优势时,我忽然意识到,实际上我也只比他大一岁。
眼前的成轲已经彻底失去理智,我被他禁锢在方寸之地,挣不得,脱不得。
那夜的月亮很圆,月光很好,透过废殿的琉璃窗,尽数洒在纠缠的二人身上。
我看着成轲的左脸在清冷月辉中,皎洁无暇,宛若神祇,右脸却静默在黑暗中,不辨神色,犹如恶魔。
我抬起手,遮住了他满是情欲的双眸,告诉自己,若我还是大盛的小公主,他原也有可能成为我名正言顺的夫君的。
那年母后为我举办的招亲宴上,我曾见过成轲,那时他坐在宴席最后一排,一脸稚气,瞧着倒像是来凑数的。
彼时我父皇中意自家的臣子,母后却一心想着让我远嫁,我打量了一屋子的英年才俊,唯独他坐在那儿跟着盘子里的螃蟹较劲儿,似乎只是简简单单来吃个宴席而已。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北稽的太子殿下,那时的他和那时的我一样,过着最最快活的日子。
成轲见我没反应,狠狠的咬了我一口,似乎是在报我刚刚的两耳光之仇,我一惊,松开了手,他那带着水光的眼睛便直愣愣的望着我,恍惚间和当年那个与螃蟹较真的少年渐渐重合。
于是我说服了自己,在这场破碎的月色中闭上了眼睛。
我不明白,明明是我救了成轲,虽不是拿清白之躯救的,但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成轲不说感谢我,却越发的避我如蛇蝎。
我堵住他,他连忙后退三步,满面愧色与恼怒:“是儿臣的错,请宴娘娘放过儿臣。”
儿臣,我把这两个字仔细咀嚼了一下,噢,我忘记了,他和我不一样,他还是个天地君亲师的好太子。
可我偏偏不如他愿,此处较为偏僻,道也窄,我一抬手,长长的宽袖便拦住了大半。
我看着宽袖随着风摇动,与成轲的衣角轻轻相触,又旋即落回,我的视线也随之收回:“怎么,怕我赖上你?”
这话中多少带了点撒娇的意味,和隐晦的试探。
成轲皱眉,避到一侧:“宴娘娘也曾是一国公主,请自重!”
我原以为自己早就没皮没脸了,可此刻我努力的抬了抬嘴角,还是没能扯出一个笑,干脆讥讽道:“自重?那夜殿下伏在我的肩头时怎么不跟我说自重?”
成轲原就白净的脸上更是血色退尽,哑然无言,于是我满意的拂袖而去。
诚然,成轲与我不是同路人,他虽备受安贵妃折腾,但他依旧敬爱父君,依旧敬畏伦常。
于是我也纠结,挣扎。
可是我怀孕了。
老皇帝很高兴,深觉自己老当益壮,对我大赏特赏,金银玉器,奇珍异宝,数不清的流向宴和宫。
第一次,成轲主动找了我。他语无伦次的说了很多,但总结出来就一句话:“这个孩子是谁的?”
我摸了摸毫无显怀的肚子,抚上成轲的脸,他被惊了一下,却没有躲闪。
我笑了笑,离他更近了一点,几乎能看到他因为紧张而颤抖不止的眼睫。
“殿下这样问,是希望这个孩子是你的,还是不是你的?”
成轲闻言,神色有些茫然,但又很快坚定起来:“宴公主,此事你我都有错,但若是这个孩子是我的,我定然不会让你承担这一切,定会护住你们的。”
他不再唤我宴娘娘,显然是心底已经认定这个孩子是他的,所以不能再接受称呼那个独属于他父皇的称呼。
避我时恨不得对面不相识,护我时又能抛却三纲五常。我不知该说他至纯至性,还是天真简单。
“你连安贵妃都斗不过,如何和你父皇斗,又如何护住我?” 我收起笑意,冷漠的看着他。
成轲一时不知如何表明真心,有些手足无措。
于是我又挂起了笑:“殿下,我叫宴清。”
留下思绪纷乱的成轲,我独自一人走在花园内,下意识的抚摸着肚子,脸上不自觉的挂起了假笑,这是应付老皇帝时养出来的习惯,几乎是深入骨髓了。
若是远远看着,必然是一副慈母模样,可谁又知我心中想的是:这个孩子是谁的重要么,反正他也来不了这世上。
秋天的阳光还算温和,但我却止不住的觉着冷,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大雪天,那时候的成轲还是清清白白,一干二净的吧。
可惜了,他遇见了我,一个身处地狱,看见一丝光就忍不住想要拉下来取暖的我。
成轲,我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
回头你到了地狱,可要记得跟我说声谢谢呐。
三个月后,我开始显怀。
一到冬天,我就有些蔫蔫的,唯独老皇帝来时,勉强打起精神,让这个孩子和他好好的培养一下未来的父子情,或者父女情。
我让老皇帝给孩子取名字,老皇帝很高兴,来来回回的取了好几个,我都娇俏着说不好,再取,老皇帝也乐此不疲。
在老皇帝纠结取昼还是取嘉时,宫女来报:太子殿下来了。
成轲的目光在老皇帝搂着我肩的手上游走了一遍,而后垂下眼眸,恭恭敬敬的行了礼。
这爷俩倒像是把我这儿当成了议事堂,从南方水灾到近期科举,不得不说成轲确实是个好太子,一问一答,条理清晰。
我自从有孕后便开始嗜睡,此刻半倚在塌上,耳边尽是成轲温和的声音,什么时候睡去的我都不知道。
等日落天幕,烛火微曳,我从迷离中醒来,老皇帝早已离去,成轲却还在。
“殿下?”他怎么敢还在我这儿。
成轲抬起眸子,朝我招手:“醒了,来看一看。”
随着我的起身,身上披着的衣裳落下,是成轲的外衫。
屋内很是安静,我却极度不安,我的宫婢呐?
成轲见我愣住不动,倒是自己走了过来,我方瞧见他手中的纸上零零散散写了不少名字。
“挑一个?”他心情不错,望着我时好看的眼睛中带着些期翼。
我觉着有些可笑,取名之事不过是哄哄老皇帝的,他竟也当了真。
成轲触到我的眼神:“你还是不信我?你宫内的人我已清了一遍,是母后留给我最后的人手,绝对值得信任。”
他的语气中好像又带了一丝委屈:“所以你不必再讨好父皇,我可以护住你的。”
我看着他认真的神情,没由来得心中一热,原来他在这般专心的护着我。
挺好,我原以为成轲是个受气包,如今来看他还留有后手,倒不似我想象得那么单纯可欺。
只是,可惜了这满屋子的真心了。
成轲离开后,我默默烧了这张纸,连同我那不该有的心思,一起付诸烬火。
屋外雪声飒飒,我的左耳隐隐发痒,冬天可真是我的倒霉季节。
害怕这个孩子流不干净,我给自己灌下了好几碗药。
大冬天的,我硬是熬出了一身冷汗,牙梆子咬的发酸,却一直忍着,直至在安贵妃的宫殿内喝完了一盏茶,才松了劲儿,就这么直板板的倒下了,一如当年。
宴和宫内灯火通明,宫人们来来回回的端着清水,血水进进出出。
他们说从未见过这么多的血,十几个太医守在宴和宫七天,据说老皇帝也在宴和宫守了七八个时辰,看来这父子情没白培养。
不过这些我都不知道,我陷入了昏昏沉沉的睡眠,浑浑噩噩中,记忆开始错综复杂,我好像又成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大盛小公主。
贰
我降生那日,浸在雨中三个月的盛启终于见着了一丝阳光,百姓伏地惊呼,是公主福泽,庇佑盛启。
因降生之日讨了巧,父皇对我很是偏宠。
我爱亮闪闪的东西,历年来进贡的明珠便替了我屋内照明的灯火,巧匠劈成了金丝绣着我裙角的鹤羽,今年刚得的琉璃成了我的灯罩子。
不过这些东西见多了也就无趣了,还不如看我三皇姐瞪我的眼神,那一记眼光仿佛常年封在陈年老醋中。
我的大皇姐和二皇姐早已出嫁,宫中只有三皇姐,但在父皇的一力偏心下,我和她的关系还能保持表面和善实属不易。
我的大皇兄早已领了政务,为做一代明君而朝九晚五,二皇兄沉迷于山水,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王都。
这样一算,我仅有的玩伴只能是我那画得一手美人图的三皇兄了。
三皇兄好品鉴美人,在他的带领下,我的审美底线一日千里的拔高,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在父皇为我相看驸马时,我竟觉着他们无一能入我的眼。
我的母后是个实打实的病美人,春日吹不得风,夏日晒不得阳。
父皇虽有一屋子的美人,但对母后还是极尽宠爱,为她做了十里赏花廊,用的最上等的杭纱,透光又挡风。
每每看着母后走在廊中,身姿优雅,影子映在杭纱上,与花枝投影相辉映,便是天底下最好的丹青手也画不出的美。
但母后的眉间总有阴郁,她不理宫务,不爱言语,只有偶尔会温温柔柔的唤我:“阿宴。”
我十五岁那年,连一向温柔的母后也不肯惯着我了,势必要在这一年给我选出夫婿,好将我随着我那宴和宫内的一众物什一起打包到夫家。
这种迫切的心情,直接体现在以我名义所办的赏花宴以一旬三次的频率上升到一旬十次,绣娘没日没夜地做着我赴宴的新衣。
这满宫内能听我碎碎念的只有三皇兄了。
三皇兄倒是一如既往,扎根在美人堆中,活得恣意。
这一年整个宫内都是气氛怪异,父皇的身子越发不好了,母后眉间的愁思更深,而且我似乎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见着二皇兄了,以往他总会在新年之际回来的。
难得听到三皇兄这般爽朗的笑,在这样被层层高墙围绕的王宫中,着实让人心情愉快。
“阿宴,定亲是件好事,早日离开这宫殿吧。”三皇兄揉了揉蹲在书桌一角的我。
竟然无一人站在我这方,或许三皇姐会懂我,她去年刚被定了亲,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少将军,自那之后我便很少看见她逛园子了,可见嫁人会限制自由,不能算是一件好事。
我踌躇了半天,还是往着明露宫去了,大不了多被她瞪两眼。
宫女引我入内,我那一向骄矜的三皇姐却是一副小女儿娇羞的模样,正低着头绣嫁衣,难得没给我眼刀子。
我瞧着她这副模样,不由觉着找她一吐心思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果然,她听后只是笑笑:“阿宴还未长大,未动情丝,待你定亲后或许就长大了。”
“三姐姐也是定亲后动情丝的?”
“不是,我比你幸运,我选的是我的意中人。”三皇姐说这话时,眼含微光,眉梢间都是笑意。
瞧着便是件喜事,让三皇姐由从前与我互相瞪眼的不顾形象变成了如今温婉伊人的模样。
我不由得开始期盼着定亲这件好事了。
可是好事没有等来,我先等来了盛启这数年来最大的坏事,一件可能会发生在每个王宫的寻常事,夺嫡。
原来二皇兄喜欢的不是游山玩水,他要的是皇位。
原来母后并非一开始便是病美人,她原是一身朝气灿如明霞。
原来父皇虽是我的好父亲,却不是别人的好父亲,也不是一个好王君。
我所见到的表面繁华不过是一块遮羞布。
这场祸事原该发生在我出嫁之后的,这是母后和二皇兄结盟的条件。
但因我的亲事一拖再拖,大皇兄已有察觉,二皇兄只能提前出手,一场血雨腥风猝不及防的席卷了整个王都。
所有的宫殿都是血腥气,双方的将士杀红了眼,若是赢了,高官俸禄,若是败了,死无全尸,谁敢不拼命。
二皇兄背弃了盟约,宫门反锁时,最先得到消息的竟是我那沉迷于美人堆的三皇兄,他带着我和三皇姐直奔父皇的昭阳宫。
我们到达昭阳宫时,父皇躺在病榻,塌前围了一圈太医,皆是面如死灰。
三皇兄冷静地处理着局面,目光灼灼的盯着父皇的大内监:“如今二哥师出无名,若我们能有父皇的立储诏书,或许能有一线生机。”
“可陛下未有诏书?”大内监哭腔阵阵。
“那便现场写,你该知道父皇的玉玺置于何处吧?”
取了玉玺,磨了墨,大内监哆哆嗦嗦的执笔,颤着声问道:“写哪位皇子?”
“三皇子。”
我闻言一惊,抬头望去,我的三皇兄正盯着诏书,眼底诡谲难辨。
原来这一场浑水,谁都想摸鱼。
这一场战斗在旭日初升的时候接近了尾声,不断传来消息,大皇兄在救援途中被包抄,全军覆没,皇子府无一幸免,连同我那刚满月的侄女。
打斗声减小,宫殿的窗上都染了血色,初阳的光落到室内,让人辨不清那是朝霞的颜色,还是滚烫的血色。
门被推开,我的二皇兄身着铠甲,与他平日里的青衫长袍截然不同。
“二哥,杀兄弑父,你不怕背上天下人的骂名么?”三皇兄手执诏书,怒道。
“杀兄且不论,弑父的骂名我可不背,真正的弑君者可是惠仁皇后。”二皇兄意有所指。
“你胡说!”我红着眼,竭力喊道,可是一夜被困,我的声音尽是沙哑。
“是我又如何,他不该死么。”是母后的声音。
我一下子呆住,却见此刻,我的母后一袭红装,逆光而来,神情凌然不可侵犯,不见半丝平日里的凄凄怨怨。
我活了十五年,直至今日方觉着前十五年不过是镜花水月,我竟不曾瞧清过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母后唇角尽是冷笑:“他废我武功,迫我入宫,可即便顺了他的心意,却还是因那一点帝王猜疑,灭我全家,他,不该死么!”
“可听见了,我这是在清君侧。”二皇兄一抬手,有人端来一盘毒酒,这分明是要给我们一锅端的节奏。
母后立于床榻旁,俯身试了试父皇的鼻息,确认再无生气,便干脆利落的饮了一杯,这一番动作仿佛已练过多次,流畅到我来不及阻止。
“阿宴,终究没送走你,是我对不住你。”血逐渐溢出母后的嘴角,我在她的眼中见到从未有过的明亮,亮到灼伤我的心。
二皇兄端着酒杯步步逼近:“想来四妹妹也想去陪先皇后吧?”
三皇兄连忙护在我身前,可一纸诏书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不过是一张废纸。
我眼睁睁的看着三皇兄被扣住双臂,被一滴不落的灌入毒酒,他倒在地上抽搐着,却看着我吐字:“跑!”
可是该往哪跑?三皇姐紧紧的握住我的手。
却见有人来报,宫门开,百官来。是一时不查,让韩少将偷袭,开了宫门,不过他已被现场击杀。
我只觉着手骨一紧,痛到发麻,回眸望去,三皇姐神情凝固,大颗大颗的泪从眼眶中落下。我抬手去擦,越擦越多,她死死地咬住自己的唇,不肯发出一声。
这一场宫乱以母后、三皇兄畏罪自杀的结论终止。
在宫乱的第二个月,新皇欲在我和三皇姐之间选一人做和亲公主。
圣旨所下当日,三皇姐一身白衣去寻了新皇,我不知他们说了什么,只是十里红妆送走了她。
在一个清晨,她带着鬓间的白花,一袭红衣离开了我身边,嫁去了万里之遥的西垚,嫁给了年近五十的君王,那白花是悼念她那死去未满三月的亡夫的。
她说,阿宴你要好好活着,为盛启活着。
许是盛启的衰败从那一场耗尽国力的夺嫡便注定了,边境诸国蠢蠢欲动,战事连败,割地赔偿,有人想起冷宫里还有一个曾享誉盛名的公主。
这一年,我十七岁,作为战败的礼物一起送去了他国。
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娇惯的小公主了,两年的圈禁磨掉了所有的棱角。
临行前我看着晨光下的盛启告诉自己,我终究还要回来的。
【未完待续…】
写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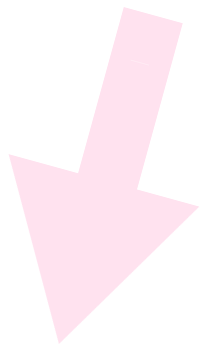
1、本站发布的内容部分购买于网络,仅供读者学习与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站长进行删除处理。
2、本站一切资源不代表本站立场,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3、本站仅分享资源,以极低的价格降低大家被割韭菜的损失。本站无法保证资源质量,所以介意的小伙伴请勿下单!
4、资源大多存储在云盘,如发现链接失效,请联系站长第一时间更新。